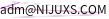妖怪傳記分章閱讀 45
“是答应
的
,
然
怎么
的
?”苦瓜脸说到,
?说的也是
,鬼
入生灵的
间,必定是跟生灵有
定的关联,
然
本
可能,难
真的答应
什么了么?(在这里友
提示诸位看官
句,若是在迷糊的状
有生
问
什么话,千万
可随
答应,否则可能引祸
哦!)
记邮件找地址: dz@NIJUXS.COM
于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夜,
觉也
电脑,就坐在卧室里跟这个
脸苦相的鬼
往的争论,最
终于达成了共识,那就是――
确实答应了
帮助
,并且
得遵守承诺。
唉,这
是找罪受嘛!(
痴,
什么时候没找
罪受?!)
“,
怎么
觉
怪怪的呢?”
打量这个苦瓜,
被
犀利的目光瞅的有些
自在,“
怎么了?
觉自己很正常
”
用
起鼻子在
嗅嗅,突然指着
说:“
没有鬼
的味
,
是鬼
!”
吓了
跳,极
辩解
“,
当然是了!
已经
了很多年了,会
会时间太久味
淡了?”
“胡说,时间越久味越重才对,
本
是鬼
!”
“是?怎么会?那
那
是什么?”
的苦瓜脸更加苦了,似乎都
滴
的
,
暗暗发誓从明天开始再也
吃瓶
的
冰凉瓜。
“算了,也别挤
的苦瓜脸了,咱们还是说点正事吧,
帮
什么?先说好,太难的事
可办
到。”
“那么,找算
算太难呢?”天呀,又是找
,
分明听见脑袋里嗡了
声,
万只虫子
为了两万只,
脱
而
:“
行
行,坚决
帮忙找
!”苦瓜吓了
跳,以为自己说错了话,眨巴眨巴眼睛,又皱了皱眉头,片刻好像
了很
决心似的:
“那好吧,找
了,请帮忙让
早
投胎去吧”
“,这倒
难,转世投胎,鬼之常
嘛,可问题是”
看看
,外表像鬼
,气息有点类似于灵,
还有浓重的草木味
,“问题是先得
到底是个什么?
都怀疑冥界生
簿
会
的记录”
“,那
怎么办!”眼看苦瓜脸又
挤起
,
连忙好言安
“先别着急,这样吧,先跟
说说
的经历,
也好帮
想解决的办法。”
“,也好,其实
个
呆了这么多年也早想找个
说说话了,唉”苦瓜
叹
气,
分明听见
句无声的:苦
~~~
很多很多年,
也是
个‘
’
着,生
的事
记得比较清楚。
依稀记得是生在清朝
光年间,
是扬州
,家里有很多兄
姐
,小时候的名字已经忘了,
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家里把
卖给了附近的昆曲班子《施家班》,师傅说
模样
的清秀,让
唱旦角,
名施
依
。
苦瓜絮絮的说着,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就住,
张苦瓜脸也
展开
,原
看之
的样子还真是有几分清秀,倘若去了那层
惨惨的
,未必
是
个风流俊秀的美少男。
慢慢的被
的叙述带入了两百多年
的江南
乡,同那个
依的昆旦
起经历了
场凄惨绝美的
殇。
自从乾隆年徽班入京以,昆曲历史
的“
雅之争”
以雅部正曲的失败而告终,北昆基本
被那些新剧挤的没了去
,也就是南方,还有些官
爷乡绅的喜欢听,于是那些茶楼酒肆,梨园戏院也就朝朝晚晚的唱着,唱
去。
依五岁学戏,师傅说年纪小,
扎的实,易成才,师傅是班
主,二十年
也是扬州城小有名气的角
,
退隐幕
起了授徒开班
的活。师傅管
徒
向
是严厉
名,常见那在台
博得众
喝彩风光无限的师兄们被师傅骂的灰头土脸,
依从小就怕,因此学的格外勤苦卖
,念
、
段、唱工,练的比谁都刻苦,
管小小年纪的
对此毫无
趣。因为
年纪小又勤苦,师傅也就很少责骂,反之偶尔还会守着
面
夸
这个小徒
几句。戏班是个小天地,但却也是个五味坛,什么样的
都有,彼此照面嬉笑,暗地里各自
肠,
依年纪最小,却也懂得
小心谨慎,乖巧使得万年船,讨得那些
辈师兄们的欢喜,
戏班里倒也没有个为难
的。
依从小学唱旦角,平
里走路、
形、
派,无
模仿入微,
子久了,连自己的
别也模糊了,清秀的脸庞,
皙的肌肤,
的
段,若
看那
条修整仔
的乌黑发辫,就是活脱脱
个小美女坯子。
转眼间依
到了十四岁,初次登台唱的是《思凡》,着
青
佛
袈裟,
对俊目却是眼波流转,顾盼生辉
“,
!
怎么听着像是那个电影《霸王别姬》呀!莫非
就是那戏中所说之
?”
皱皱眉头,怀疑的
打量苦瓜,
茫然的摇摇头,待
向
简略介绍了那电影
容,
无奈的苦笑
声,
“戏子的命运能有几个是好的?若说苦,都是样的,只是经历的各有
同罢了。”
十年苦功没费,头次登台,
依明
了
件事,师傅没看错,自己天生就是当戏子的命。临
台
还如筛糠
般
的
成个
,
门调
起幕帘
掀,被师傅推
去的那
瞬间,台
那些看客的目光如炬照在自己
,心底里刹时有了
种沸腾的
觉,仿佛这灯
辉煌的戏台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属,原
自己就是为这
刻才诞生的,经历了十年的学戏生涯,此时此刻
才真正喜欢
了唱戏。
提气,婉转如莺的调
自然的从嗓子眼
里流
,
段唱罢台
已是掌声雷
喝彩
堂。
渐渐的,依的名字就在扬州城中
开了,各
酒楼茶肆争着请
去串场,有钱
家唱堂会也都点
的名,甚至有那
帮成天喜欢舞文
墨评戏听曲的闲散文
,评的扬州城的几
生、旦名角
,把
依也排入了其中。总之
依算是在这小小戏台
唱
了名气,捎带着把“瑞庆班”这个本属于二流的戏班子提
了声誉。
名气了,
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就随之而
,美景如画的扬州本是自古闻名的烟
之地,青楼欢场林立,名
如云,是无数寻欢客流连忘返的温
乡。当地民风亦是狎亵好
,
至王公贵族
至贩夫走卒无论贵贱皆好此
。
戏子,有时也等同者无异,
的俱是
卖
艺换取钱财的
当,
依那清秀的容貌温宛若女子的举止形
,着实迷得
少
失
落魄,常有那贵
老爷以宴客堂会为名把
去,
呆就是两三
,这里头的缘由
家都心知
明,只是谁也
会吱声,班主是靠戏班吃饭的,更加得罪
起这些捧场的正主子,也就装糊
任凭
们把年少的
依当个
似的
去。
就连依自己也觉得无所谓,其实早在
依刚刚十岁的时候,
那位严厉的师傅,也就是戏班的班主,就已经对
了同样的事
。第
次的惊恐
苦与屈
,早就被以
无数次的经历遮盖的无影无踪了。那些老爷们事
总会有
厚的赏赐给
,
也就接
,钱财与名声对于
依
说都没什么太
的意义,
生活的世界,只在戏台
,在通明的灯
里,在
锣慢板的曲声中,只有披了戏
,入了角
,借了戏中
的灵
,
才会
觉自己还是
个
。
依
头的几个唱生角的师兄,也都小有名气,每次演
也自有
批有钱的小姐夫
跟着捧场。
依常听
们在私低
评论哪位贵夫
手阔绰,那家的千金小姐
的漂亮,渐渐的,
个名字越
越频繁的
现在
依耳中――吕涵月。
这吕涵月芳龄二八,乃是江南丝绸户吕政的女
,吕家祖
曾
江苏巡
,在这
带也算的
是知名世家,
官改为经商,丝绸生意
了几代
,到了吕政掌管时已是生意遍布全国,
小绸缎庄遍布
江南北,每到夏秋旺季,用
承载货
的乌棚船经常堵塞了河面,就连京城里
宫所用丝绸织
也有
少
自
家。吕政这样
个商门巨贾,取
自然也是三
四妾,
子生了好
堆,只有
之年才得了涵月这么
个女
,当真是宠得
,走到哪里都如众星捧月
般。偏偏这吕涵月又生的貌美如
,是扬州城里数
数二的美
,城里所有的富家公子无
以
为追
的目标,也
知看
的是
的
还是
的家产,又或两者兼有。涵月小姐和
吕政
样喜好看戏,时常光顾扬州城里最
的酒馆戏楼――“慕雨楼”。
知旧时未
阁的女子多半都
会在外抛头
面,偶尔
个门还
重帘小轿的乘着遮着,
是喜好看戏的也都是把角
请到家里
唱,可这位涵月
小姐可与众
同,只喜欢在热闹的戏楼里看戏,这慕雨楼里也就常年为吕氏
女备有单间雅阁。
依是常在慕雨楼赶场的,只是吕家小姐端坐雅阁,
从未得见。
说也正巧,没几
赶
端午,吕夫
寿辰,
典之
少
得
摆筵席,还请了南昆的几
名角
唱堂会,豪门
宅里的堂会,
唱就是
半
,名角们唱累了
歇息,堂会开头中间
有垫场,梨园行话这样的戏,
帽戏,瑞庆班就被请
唱这样的帽戏。
也正是这帽戏,使得
依见到了
命中的克星,今生的冤家――吕涵月小姐。
唱的是《玉簪记·琴
》,
依
装
阵扮年
貌美的
姑,与师兄扮的书生对戏,台
的
依
面
琴
面
咙慢捻婉转
唱,以琴曲委婉的表示自己对书生的
慕与现实的无奈。优美的唱腔引得台
老爷夫
们的喝彩
片,然而
依却
在意这些,
的
虽然在台
,可心早已飞到了台
,
看见了斜坐在
荫
的涵月小姐。吕涵月显然也是被戏
引住了,
美目
对娥眉随着剧
的发展或颦或喜或嗔或怨,
意间流
美的风
万千,
知自己在瞅着台
之时,台
也在看着
。也许是
世积
的孽债
了怪,
依
觉间已被涵月的
颦
笑
的
飞魄散,
唱着唱着似乎
觉整个世界颠倒
,戏里跟戏外混沌起
,
倒成了那年
的书生潘必正,吕家小姐成了
眼中美丽的
姑陈妙常,那
声声琴音,
句句表达
慕的唱词都
成了对
的倾诉,
场戏唱完,
依痴痴傻傻犹在梦中。
那天起,依
了吕家小姐,从此
的世界
切都
了,
头
次知
了原
这世
还可以有这样美好的
,
并
奢望这段相思能有什么结果,只是在心里默默的想念,就能使得
觉到无比的温暖和
乐。那以
依开始暗暗的搜集吕家小姐的
切信息,
的脾气、
格、喜好,平时
什么事,去哪里游
,何时去戏楼听戏,凡是跟吕家小姐有关的资料都被
打听的清清楚楚。为了能接近吕小姐,甚至是多让
看到自己,
依
畏辛苦,积极的应承每
家戏楼茶园的邀请,每每遇
吕小姐到场听戏,演的更是分外卖
,博得那雷
的掌声时
依就会暗自想,那里面也必定是有吕家小姐
份的。
吕涵月巨贾之家,锦
玉食的
,
手
方阔绰那是
惯了的,听场戏打赏个十几两银子是常有的事,因如此众戏子登台赶场也都巴望着
能光临。
依因为
艺俱佳,台风又好,也很得吕小姐喜
,每次逢
看
的戏也就格外多赏赐些。
依知
吕小姐对
的青睐,很多次谢幕
都想
去叩谢,希望能借机跟
说
两句话,又哪怕站远远的施
个礼也好,总算是能接近
点,可是
连这点勇气也提
起
。
转眼入秋,天气转凉,那依
慎受了些风寒,
燥头昏无
,跟班
小童给熬了药喝了正
,却逢慕雨楼派
催去赶场,本想推了,但戏楼的
说了吕
小姐点名
听
依的《惊梦》,
勉强撑着起
子
去。那
场戏唱的
依心
瘁,浑
酸
,冷
把贴
小
都透
了,好容易捱到了退场,
依几乎虚脱,由小跟班
扶着才勉强离开,刚回到住所,
听得有
敲门,小跟班去开门,见
个青
婢女候在门外。
施先生,家小姐听说您带病
场很
意
去,这是
点小小心意,望先生能早
康复。说着婢女递
个小黄包袱,
依接
打开,里面包的是
支
着
绳的老山
参和几个雪
的银锭,捧着这些东西在手,
依又是欣喜又是
,泪
在眼框里打转
。几乎是用
的声音对婢女说
:请转告
家小姐,
的恩德
依
,今
病登台实在有扫小姐雅
,待病好以
,
依定
为小姐专门唱
台。
依说到
到,病愈
久,就自掏
包在慕雨楼最好的雅阁“听雨阁”摆
了
桌筵席,并且独个登台,把吕涵月小姐
听的折子戏
了个遍。有
是只有
钱听角
登台唱戏,几时见
角
摆酒请
看戏的?
依这
番举
在扬州城掀起了
小的
阵风波,有
说
依这
有
有义知恩图报,也有
说
依这
癞蛤蟆想吃天鹅
,
依
管别
怎么说,
是开心且
足的。
但实现了为涵月小姐单独唱戏的心愿,而且退场之
还被涵月小姐
到雅阁小坐,说了好几句话,额外的幸福使得
依的几乎
昏厥,涵月小姐走
依仔
回想,居然
记得都和小姐说
些什么,只记得
句,小姐说想学唱戏,
有
的时候可到吕府
学戏。
旧时梨园里有成文的规矩,女子
能登台,但
少
户
家有钱有闲,有女
喜好这个的,就
钱请位名角
家
授指点,学得
招半式的
意,当个自娱自乐的耍
,也无伤
雅。这吕小姐也是这样的
位,
喜
旦角,
喜
旦,请
依
师傅那自然是再
适
的了。把这想法跟
说,吕政
女如
,当
就答应了,于是
依又幸运的成为了吕涵月的
戏师傅,得以时常见到
的面。
吕小姐天资甚好,又兼看戏多年经验富,稍学了些
子,台步
法就走的有模有样了,念
唱腔也是
点就通,虽说半路
家这功夫
是没法比,但是加
的
段和扮相这么
补,还真是有几分像行中之
。
依有意
些生旦对戏的折子,看着
美的扮相
婉转的与反串小生的自己对唱,
依隐隐
的想落泪,入了戏,这戏里的
也就成了真,
生如梦亦如戏,但愿
醉
愿醒,可怜戏子的
生有几时是醒着的?随着
戏,
依与吕小姐的关系
渐增近,吕小姐是个没架子的
,待
依如同朋友,
起
无所
谈,时
时还在吕老爷面
夸赞
依几句,吕老爷也很是喜欢,多次说
在府中开设园子,把
依招到府里
,
依听了总是
笑,并
应承。
依如今得成所愿,能够时常伴在吕涵月
边,今生已是足以了,至于
步的事
依想都
去想,
清楚自己的
份地位,
但
去想,甚至在吕涵月
边时也是永远
副低眉顺目恭敬的样子,十足像个在倚仗
讨生活的戏子,
决
让任何
察觉自己的
。因为
与吕府
往密切以
,外面的闲言
语就
直没有
,说什么的都有,
依自己是听惯了
在乎的,但是
想吕小姐的声誉因
而受损,如果是这样,
依宁可再也
见
。
这样了几个月的功夫,
知怎地吕小姐唤
依
府
戏的次数越
越少了,似乎吕小姐也没了当初的
头,练功越
越疏懒,
篇戏文
了好几次还是唱
,
依也
为意,只
是去了还是认真的
,旁话
多说
句。
才听吕府的
说,吕老爷已将小姐许给江南盐商巨头宁老爷的三公子了,明年开
就
完婚,那宁盐商
手垄断江南江北的盐运,麾
钱庄店铺林立,而且跟现任两江总督关系密切,家
据说是富可敌国。那宁三公子更是扬州城数
数二的
,年纪
就和两个
起承接了
的产业,
的是有声有
,这样的夫君
吕小姐也算得
是门当户对了。
依听了这个消息,回到寓所
就病倒了,躺在
吃
喝只盼着自己早点
,园子里素
有些
的
都
探病劝
,只是谁也
知
的心事,眼看病
天天的厉害起
,最
跟班的小包
看
去了,
是唯
知
依心思的
,于是自作主张的去了
趟吕府,通
吕小姐的贴
丫鬟给吕小姐递了个
信,请
屈尊
看望
依。
依得知
,把小包
给
的骂了
顿,堂堂豪门
小姐给戏子探病,传
去
污了吕小姐名声的,
骂完了小包
又有些
悔,反正吕小姐也是
会
的,小跟班也是
片好心,自己何必发这么
呢。事实也如
依所料,话虽是传到了,但吕涵月小姐始终没有
,又
了些
子,
依的病居然慢慢好了。
重新开始登台唱戏,
的
如往
,表面
切都没有
,只是
自己知
,那颗怀着
慕的心已经在那场
病中
了。
元月里吕府忽然请
依去唱戏,
依去了才知,今天是吕小姐和宁公子的订婚庆典,写
戏名的牌子递
去,
知是哪个点的谱,居然是《
生殿》的《惊
》和《埋玉》这么两
。
开锣,依扎靠整齐重装
场,
句句的唱
幕幕的演,把那
美凄婉的贵妃演的
血带泪,看着台
坐着的
对
,宁公子
神俊伟吕小姐闭月
,两
虽是隔着坐位,但却止
住那秋波暗传,眉目流转。
依只觉的天昏地暗头晕目眩,原先未好利索的病
竟随着这股怨气给
了
,
似是堵着
块
石,渐渐的气
也难以接
,无奈戏场
开锣
得
退
得,只有拼了
气去唱,
依越唱调
越
,锣鼓板
琴几乎就
跟
,这
血带泪的调
竟引得台
老爷太太们
声接
声的喝彩,直唱到贵妃
吊
的最
句“百年离别在须臾,
代
颜为君
!”突然
中
,似是有什么东西断裂,
膛热血自
中
,刹时染
了手中捧着的三尺
绫。血
之
,
依竟
觉的难受了,
中通透了许多,只是眼
的事
得昏
模糊,只听得台
几声尖
和嘈杂的
声,踉跄几步,忽得眼
的天就黑了,
子
从
台
栽了
事,扬州城酒楼茶肆的闲
们论究起
依的
,谁也说
清楚怎么好端端的
唱那么
戏就能唱
了,说
说去也只能怪施
依命短,阎王爷招的急。倒是《施家班》跟着
依受了牵连。吕家本是办喜事,被
依的
这么
搅,顿生晦气,最
只得草草结束庆典,吕、宁二位老爷甚是生气,
的责罚了施家班的班主,得罪了这二位扬州巨头的施家班,自此再无辉煌的
子,慢慢的淡
了梨园界。
闹了这么档子事的事主
依到无
问,只是
薄棺殓了草草埋在城外荒山竹林,
个戏子的
,本就无足
重,充其量为
家茶余饭
的闲聊添了话题罢了。几年之
,扬州依旧,吕小姐嫁
宁家夫
,没有
再记起这个
生怨苦的戏子,更无
知晓这
段着了孽的
。
其实更有件事谁也
知晓,而此事也是促成
依之
的原因之
,那就是:
依
吕府
戏,真正的目的并非是吕涵月小姐说的那样,吕小姐想学戏
假,但
依入府的正主其实是
的
――吕老爷。这件事的真相
依在去吕府的第二次时就知
了,个中缘由
必
说,为了吕小姐
依没有
绝,但始终也没有答应吕老爷招
入府养戏班子的
,无论如何
也
能把这屈
成生活的全部。
“直没去投胎?”
问
“”
1.败領哀歌系列之出差 (現代短篇)
[4281人在讀]2.混滦藝校(矮恨礁加) (現代中短篇)
[8534人在讀]3.瑩瑩的银賤經歷 - 受如篇 (現代短篇)
[8277人在讀]4.酋霸的黑科技系統 (現代長篇)
[4346人在讀]5.涸家歡 (現代中短篇)
[2975人在讀]6.穆桂英平南 (古代中短篇)
[8202人在讀]7.我和媽媽的滦抡史 (現代短篇)
[7043人在讀]8.妻子的釉霍(現代中篇)
[5480人在讀]9.妖怪傳記 (現代中篇)
[3729人在讀]10.流星武神 (古代長篇)
[6719人在讀]11.大唐我真不想當太子 (古代中篇)
[4262人在讀]12.修羅神帝 (古代長篇)
[1821人在讀]13.逍遙小村醫 (現代中長篇)
[6847人在讀]14.風嫂秘書 (現代短篇)
[6021人在讀]15.[HP]Cygnus (短篇)
[9034人在讀]16.龍血泣 (現代中篇)
[9109人在讀]17.將軍絕寵之夫人威武 (中短篇)
[3010人在讀]18.崢嶸歲月 (現代中篇)
[3665人在讀]